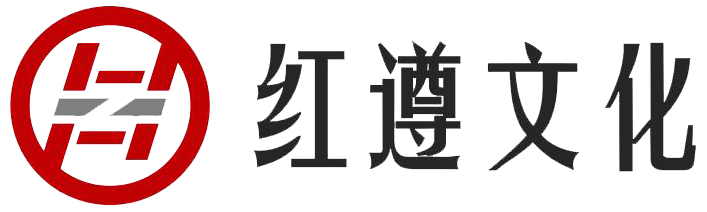遵义会议的召开由于处于战争时期,未能留下完整的资料,以致一些重要情节在党史研究和宣传中说法不一。一九八一年年底开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对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经过调查,弄清了遵义会议召开的日期、参加会议的人员、会议通过的决定、洛甫代替博古工作以及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等问题,写成了《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经中央批准,在《中共党史资料》(1983年)第六期发表。
遵义会议是一九三五年一月至十七日召开的。
1983年以前党史界对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有几种说法。《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决议》上,标为:“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但是,根据当时中央的电报和敌伪资料,证明工农红军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攻克遵义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军委纵队于九日进驻遵义,因而遵义会议不可能在九日之前召开。
那么,遵义会议究竟是何时召开的呢?调查人员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文件、电报,确定会议召开的时间为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其中最主要的依据是:一月十三日,中央以周恩来的名义发电报通知刘少奇、李卓然:“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这份纸面早已发黄的电报底稿,现在已作为珍品陈列在毛主席纪念堂周恩来革命业绩纪念室里。
1982年中央档案馆提供了一份珍贵的遵义会议传达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经确认是陈去的手稿。陈云同志在手稿中写道:遵义政治局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会议在开幕的一月十五日起,经过三天,会议结束和通过决议的日期应为十七日。这个时间在军委机要干部伍云甫同志的长征日记中得到印证。伍云甫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九时开营、科以上干部会议。洛甫报告五次‘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即一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
当时军委发给各军团的电报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时间。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至十三日,军委给各军团的电报都是发给各军团首长的,这说明当时各军团首长都在各自的部队里指挥作战。从一月十四日遵义会议召开前夕,到遵义会议结束后的十七日二十三时,由于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已离开部队到遵义参加会议,军委便中断了给他们的电报。李卓然因故迟到,只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议,军委一月十六日二十四时也中断了给他的电报。遵义会议结束后,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返回部队,军委从一月十七日二十三时起,又恢复了给他们的电报。
红军一月七日攻克遵义,为什么到一月十五日才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呢?有的同志推测在扩大会议之前是否开过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杨尚昆在回答调查人员的提问时说,当时他曾建议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然后再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但这个意见并未被采纳。后由担任中央党校顾问、当时在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吴亮平分析说,红军在攻克遵义以后,召开这样重要的会议,军事上需要部署,以保证会议的安全召开;会议也需要时间来进行准备,需要做工作,争取多数同志的觉悟和支持。
至于遵义会议决议为什么标明这个决议是一月八日通过的,现在还未查清。陈云同志的手稿说: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这说明,决议是洛甫同志在遵义会议之后才写成文字的,可能因事后追记,标错了时间。
参加遵义会议的共二十人。
经过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反复调查,当年参加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共有二十人。参加会议的人员是:
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
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
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出席会议的还有:邓小平、李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伍修权(翻译)。
过去,不少人认为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出席了遵义会议。这次调查确认:董振堂没有出席遵义会议。主要根据是:陈云同志手稿中记载的参加会议的人员中没有董振堂;董振堂与李卓然当时同为五军团负责人,中央一月十三日发电报通知李卓然和刘少奇去遵义开会,没有说要董振堂也去参加会议;遵义会议期间,军委发给五军团的电报中,多次指名给董振堂,这说明他仍然在部队。另外,在这次调查中,参加遵义会议的陈云、杨尚昆、李卓然和当时在中央军委总部工作的叶剑英等同志,都证实董振堂没有参加遵义会议。
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并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会议开始时,秦邦宪(博古)作了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副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正确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到会的许多同志发了言,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会议决议在会后由洛甫写成文字)。决议指出:“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五次反“围剿”中,“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据陈云同志传达手稿记载,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洛甫代替博古工作和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以后。
过去有不少材料介绍说,遵义会议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有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并推选张闻天为总书记,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经调查证实,这些说法都不准确。
在遵义会议上,中央在组织上只作了部分调整,政治局常委并未进行明确分工,博古也没有正式交出职权。洛甫接替博古的工作和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是遵义会议之后完成的。
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央由“三人团”处理一切。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实际上是党、政、军的领导核心和最高权力机构。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而周恩来同志仍是最高军事指挥者。这在实际上取消了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力。但当时博古的职务并未正式免除,陈云同志手稿中提到:“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红军行进到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贵州省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洛甫)接替秦邦宪(博古)的工作。当时党内没有明确设“总书记”,而是指定一人在党内“负总的责任”。
成立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则是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左右,在贵州遵义的鸭溪、苟坝一带。一九三五年三月初,红军第二次撤离遵义后,在要不要攻打敌人的坚固据点打鼓新场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后来,毛泽东同志说服了大家,红军放弃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中央感到在敌情紧急、情况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不能再过像去那样指挥了。亟需成立了一个能够机动灵活而又果断地指挥军事的权威机构。这样,经毛泽东建议,张闻天同志经政治局会议通过,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便宣告成立,全权负责处理最紧迫的军事指挥工作。这个三人小组当时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调整工作便大体完成。
《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公布已经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该《调查报告》未涉及的内容,有的在党史界取得了一致意见,如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周恩来作主、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的错误。之后,才是毛泽东接着发言。有的还需要继续作深入研究,如该调查报告对遵义会议决议标明的时间是一月八日通过,用词是“又因事后追记,标错了时间”。也是不肯定,也算一种存疑,供继续研究。
来源:遵义会议纪念馆,吴德坤